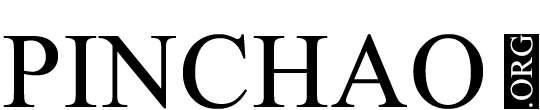
▲在当代儿童小说的艺术探索中,一方面是朝向个体的“小”历史不断得到新的关注、开掘;另一方面,一种面向“大”历史的书写和表达的冲动,始终不曾消退。
▲原创儿童文学在运用一个有长度的叙事过程表现特定的生活和情感内容方面,多了些“铺天盖地”的努力,少了些“惊心动魄”的力道。
▲多年来,儿童文学努力克服着“成长”书写中虚幻的理想主义,《星鱼》进一步提出,如何在虚幻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生活主义”之间,寻找通往“成长”的更好路径。
▲在一切传统文化题材的儿童文学写作中,除却传统文化自身的内容、内涵,作家还需思考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这种面向传统的书写所体现的现代文学意义与现代艺术价值。
2018年,儿童文学领域有不少值得一说的创作现象,值得一谈的作家作品。每到这样的时刻,总是深感语言的篇幅无法企及现实的体量。我想就这一年来若干重要的文学现象、一些典型的作家作品,来看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收获,以及是否还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小”历史与“大”历史
一切历史的书写都充满陷阱。时空相隔愈远,写作的危险和难度也相应愈增。对儿童文学来说,恐怕还要加上另一重可能的陷阱,那就是历史本身与童年生活之间的适切度与对接度问题。这些年来,原创儿童文学见证了写作者们朝向这一难度区域的不断突进。2018年,4部历史童年题材的儿童小说令人印象深刻:《有鸽子的夏天》(刘海栖)、《野蜂飞舞》(黄蓓佳)、《耗子大爷起晚了》(叶广芩)、《正阳门下》(史雷)。它们不但向我们展示了已逝童年永不褪色的生活滋味,也向我们展示着中国儿童小说独特而丰饶的语言滋味。
从《太阳宫》到《耗子大爷起晚了》,叶广芩的作品真正落脚在了儿童文学的地界。读《耗子大爷起晚了》,字句皆是轻捷舒畅而溜圆妥帖,那种生动到如有一个孩子在你耳边聒噪的叙述语言,那种如亲见这个不安分的孩子跳来跃去的叙述节奏,再没有比它更适合童年的了。《有鸽子的夏天》里简白如素而又充满蛮劲、短截稚朴而又饱含情感的语言,既烘托着叙事节奏的紧凑推进,又让人一再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琢磨它的余味,回味它的张力。《野蜂飞舞》写出了一种如野蜂飞舞般漫天席地、无可压抑的生命感觉。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曲子在黄蓓佳的笔下仿佛拥有了另一种生命,那样的欢乐,那样的悲伤,那样含着泪水的生活的微笑,叫人永不能忘。《正阳门下》的京味儿叙述畅快而欢实,底下又流动着浅淡的古意和拙趣,再底下,是没有任何暴力能够打断的生活的坚固脉流。读着这些作品,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为什么说儿童文学的简朴无关单薄,而是另一种形态的丰盈。
而这样的书写不只与童年和语言有关。在面朝历史的同时,它还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来自当下的诘问:历史因何存在,又为何值得书写?首先当然是为“人”。中国儿童文学经历过历史叙事被政治意识形态绑架的年代,那时候,历史与人的生命、生活之间的血脉关联被完全切断。由此造成的历史叙事的某些观念与惯性,给当代儿童文学带来入骨的伤害。近年来的历史童年题材写作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意义重大的艺术反拨和重写的努力。一些作品有意识地让政治事件与运动退到历史叙说的远景处,让真实的“孩子”重新回到历史舞台的中央。在《耗子大爷起晚了》等作品里,宏大历史完全被淡化,我们眼前只有一个无比生动的孩子。在《有鸽子的夏天》《水花园》(李秋沅)、《苏三不要哭》(吴洲星)等作品里,历史的大事件隐约出没,但小说的焦点还是落在个体的小历史上。这样的历史,小则小矣,却是血肉丰满,饱含体温;这样的历史,因其细小而真切,又因其真切而动人。某种意义上,文学就是为了这样细小却真切的动人而存在的。
但我还想说,在当代儿童小说的艺术探索中,一方面是朝向个体的“小”历史不断得到新的关注、开掘;另一方面,一种面向“大”历史的书写和表达的冲动,始终不曾消退。在后一种视角下,文学所为之“人”,既是个体之人,也是族群之人、家国之人。随着这类题材儿童小说艺术探索的深入,这种冲动可能正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野蜂飞舞》里的榴园与黄橙子们、《正阳门下》中的将军胡同与刘家、《谢谢青木关》(谷应)里的青木关,以及《黑仔星》(郝周)里的“黑仔星”,既关乎个人史,也关乎家国史、民族史。当个体与时代的要求、个人与民族的命运不可避免地遽然相撞,如何使微小的个体不被历史的宏大话语轻易吞噬,又如何使巨大的历史话题在细小和真切中得到真实、深刻的传递,是这类儿童文学创作进一步走向深处必须直面的艺术难题。
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再多说一说《正阳门下》的原因。《正阳门下》从《将军胡同》而来,这两部作品之间不只有着人物、地点、叙事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其中还包含了作家在同类题材写作探索方面某种突进的努力。《将军胡同》提供的鲜活、独特、令人过目难忘的个人性的历史叙说,将历史题材儿童小说对于个人史的发掘、表现推向了艺术的高点。但同时,史雷在呈现个人视角下历史生活的生动图景的同时,可能始终怀着对于人物及其生活与其身处的大时代之间的某种关联焦虑。生活之流是永恒的,但是,在那样的时代,生活又多么应该变得与过去全然不同。这或许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小说最后,他让图将军以某种形式的“牺牲”,实现了“小”个体面向“大”历史的言说与承担。从小说的叙事肌理来看,这个“牺牲”的身影,其符号性显然大于生活的逻辑,但从中恰恰看见了作家对“大”历史及其代表的更广阔世界与生活的某种执著。换句话说,面对一个风云激变的时代,“小”历史的书写并不能让他感到完全满足。
我愿意相信,正是这份未得满足的执著,进一步驱动着《正阳门下》的写作。在《正阳门下》里,史雷把原本熟稔的个人史笔法小心地搁在手边,开始尝试另一种历史的编织。同样是以老北京胡同的日常生活为底色,在这部小说里,民族的、国家的而非个人性的冲突,贯穿首尾。二舅带着“我”驯鸽子的场景,是小说中最具俗世生活趣味和意味的片段,就在它生活游戏的表象之下,却不时隐现着“成为中国最好的军鸽”的政治暗示。二舅最后成为中共地下党,呼应了上述暗示。大舅呢,“国军少将”,哀时局而扼腕,最后被二舅疑似成功“策反”。这样单纯而“理想”的安排,使小说多少带上了王安忆说的那种“男孩子气”,而没能再为读者奉上又一位像图将军那样有着更丰满的复杂度的生活形象。但透过这种“男孩气”,我们却也看到了作家试图带历史童年叙事冲破私人生活领地、重新闯向历史宏大舞台的野心。
这是了不起的文学的野心。在《野蜂飞舞》未出版稿的红楼研讨会上,黄蓓佳坦言,身为一个作家,面对这样一段壮烈的历史,如何能不充满为它发声的强烈愿望?但这样的言说同时也充满了艰难。《野蜂飞舞》最后,我们同样看到,黄家长大起来的三个孩子,分别加入中国远征军、国民党空军和共产党,先后为报国牺牲。如果再把目光放开去,在近年热播的近现代历史题材电视剧中,也常有相类的叙事处理:通过向同一家族的各个成员分派不同的历史身份,使之构成关于那个时代宏大历史的符号性隐喻。这里需要反思的不是隐喻本身的文学合法性,而是如何使之在文学表达层面更为合理,更符合文学自身的要求与规律。事实上,要在生活的偶然、细碎的自然逻辑中完成对于宏大历史的呈现与思考,很可能不是单一的个人传奇或简短的家族故事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战争与和平》式的体量,或者至少是《白鹿原》式的体量。在这样的体量基数里,历史的宏大展开为可信的生活,才有了逻辑空间的充分依托。那么,对于一个客观上受到体量限制的儿童文学作品而言,书写“大”历史仍然是可能的吗?如果是,它该如何以更好的方式走向历史的宏大,走进历史之“人”的宏大?这或许是今天所有选择在写作中直面“大”历史的作家们必然要面对的困境。《正阳门下》和《野蜂飞舞》这样的作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经验,也铺垫了富于意义的新起点。
情感深度与叙事结构
2018年是狗年,有意思的是,儿童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狗”。常新港的《尼克代表我》,在小说与童话的交叉语境中展开一个似真还幻的少年生活故事。一个衣食无忧的当代孩子内心的苦闷,在“尼克代表我”的非常态宣泄中,得到了离奇而淋漓的表达。曹文轩的《疯狗浪》,在海边渔村的环境里铺开一场狗与人、狗与狗的恩怨传奇。小说中的“疯狗浪”既是实指,也是虚指。在疯狗浪一样的生存威胁下,黑风与沫沫以生命为盾牌,坚持着彼此的守护。《黑木头》里,赵丽宏把笔触转向当代都市孩子的日常生活,在狗与人重新的相互结识和信任中,书写了日常世界的某种深情况味。儿童小说《舒叶与神秘小狗》(李学斌)里的“神秘小狗”,后来身份揭晓,原来是小巴西狼,但在大部分叙事时间里,它一直被当作小狗看待和对待。不论何时何地,狗的故事总是与人的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们就来说说情感。我想谈的是曹文轩的《疯狗浪》。这些年来,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写作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对待写作的某种坚执的痴迷,这种痴迷与外力似乎并无太大干系,而是更多地源自他的本性。不论环境如何变化,他一直在写,不停地写,而且从不轻易停留在某种惯性的滑翔写作状态。在《疯狗浪》的后记中,他说:“写了几十年的作品,我总提醒自己不要安于现状,不要陷入一种无形的、驾轻就熟的写作模式。”这种写作的状态激起我们极大的期待。我们由衷地期望,在曹文轩这样的作家身上,当代儿童文学有可能实现它某种高远的艺术抱负。
在《疯狗浪》里,作家把视点移到海边,移到渔村,移到家狗与野狗眼睛里的世界。这样的题材在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写作谱系中无疑是特别的,但个中情感的质地和重量却是一脉相承。一只家狗与一只丧家的狗,在命运看似偶然的安排下走到一起,相濡以沫。沫沫为黑风放弃了温暖的人间生活,黑风则为沫沫和他们的孩子付出了生命。
这是一个令人动情的故事。但我想说,从更严苛的角度看,这部小说以一个长篇构架反复渲染的动人情感,还是运行在一种相对单维的状态里。从黑风为了拯救素不相识的沫沫飞奔而下、陷身危险的瞬间,从沫沫听到黑风受伤的吠叫掉头而来、重入罗网的一刻,这种情感就已经定形。此后,沫沫为了黑风放弃安逸的生活,甚至离开心爱的主人,都是这场生死之恋的合理回音。黑风的回报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整个故事的过程只是在印证这种情感,却没有从根本上深化它,扩大它。正如小说开始处,黑风以赴死的决心挡在沫沫与野狗之间,到了最后,它的死亡更像是起初这个未竟的牺牲举动的尘埃落定。与此相应,随着情节的推进,它们之间建立起的情感空间始终只回环在这两个角色之间,而没有激起更深广的旋流;它甚至还有意无意地排斥着沫沫的主人、小女孩船花的介入。它是封闭的,似乎只能属于黑风和沫沫自己,这就使人在同情中不免感到了某种局促。
我以为,这与《疯狗浪》在长篇结构上的处理是有直接关联的。一部长篇构架的小说,可以是围绕着同一个点的铺排与赋写,也可以是从一个点出发的步步旋进,节节推升。前者会加强情感的气势,使之如排山倒海般涌向我们,后者则将加强情感的后力,使之缓缓透入我们的灵魂和骨髓深处;前者铺天盖地,后者惊心动魄。《疯狗浪》的结构更接近前者。小说中黑风与沫沫的情感,从一开始就是生死抉择、超越寻常的,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不寻常性不断得到证明,以至于到了最后,若非黑风的献身,似已无法再将它推向结局。可以一问的是:一种生死与共的情感,除了愿意为彼此不断地付出一切,还有什么?
请允许我们对曹文轩的写作怀有苛求,因为这个写作本身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因为他的写作始终望向更高的地方,还因为谈论曹文轩时,我们不只是在谈论一个作家,而常常是同时在谈论一种重要的写作现象、一个重大的艺术话题。我想说的是,原创儿童文学在运用一个有长度的叙事过程表现特定的生活和情感内容方面,多了些“铺天盖地”的努力,少了些“惊心动魄”的力道。2018年出版的《你的脚下,我的脚下》(西雨客)、《莫里》(陈帅)等作品,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阅读惊喜,但在最终抵达的情感的震撼力和穿透力上,又有令人不满足的遗憾。究其原因,结构的隐在问题不容忽视。准确地说,这种不满足指向的不是一部作品的缺憾,而是对于原创儿童文学实现其更高艺术突破的期望。
“爱”与“成长”的再思考
儿童文学有两个具有普适性的主题:一个是“爱”,另一个是“成长”。这些年来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几乎都能从这两个童年生活的母词里找到主题的归宿。这一现实也反过来印证了“爱”与“成长”的题旨之下,其实包含了作品具体生态的千差万别。今天,面对一部作品,需要讨论的可能不是它是否表现了“爱”或“成长”,而是它表现了什么样的“爱”和“成长”。
让我们来谈一谈《人民文学》2018年第6期发表的一部童话《星鱼》(周晓枫)。对于2018年的原创儿童文学,《星鱼》的出现有两个重要的代表性。
第一,它是《人民文学》2018年第6期上发表的13种儿童文学作品之一。该期《人民文学》系儿童文学专刊,从童话、小说到诗歌,从城市、乡村到幻想世界,我们读到童年轻盈的欢笑,也读到它静默的哭泣,读到它精灵般的飞翔,也读到它寓言式的深思。《人民文学》在2018年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童年和儿童文学的关切,也回应了这些年来儿童文学这一文类聚集的社会热度。
第二,它代表了近年引起关注和热议的成人文学作家参与儿童文学写作现象的持续铺展。发表在《人民文学》2018年第6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作者中既有翌平、陆梅等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也有不少从成人文学跨界进入儿童文学写作的作家,如周晓枫、李浩、蒋一谈等。此外还有前面提到的《耗子大爷起晚了》,以及今年出版的《砖红色屋顶》(马原)等作品。我们看到了这些作品为儿童文学带来的丰富的语言、宽阔的生活、厚重的精神,同时也看到了从成人文学到儿童文学的写作,绝不是跨越一道读者对象的门槛那么简单。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们不得不谨慎应对的艺术难题,正是儿童文学自身艺术难度的显现。
周晓枫在创作谈中说,《星鱼》是她的第二个童话作品,是“关于梦想、自由、亲情、成长、友谊和责任的故事”。童话从一个富于童心而气势恢弘的想象开始:海洋里最大的鱼类鲸鲨,原是天上的星星变化。小弩从“幸福”“完美”的天上生活选择坠向地面的姿态,带着某种弥尔顿笔下“失乐园”的悲壮气象。随着小弓的陪伴坠落,小弩的世间生活成了一场寻找的旅途,它也由此经历了另一种“什么都有可能”的丰饶、奇妙同时也充满危险的世间生活。
最终,小弩找到了小弓,后者奄奄一息,继而失去记忆。小弩的内心充满了对小弓的负疚和悔罪。我们看到,小弩在海洋里学会了“爱”,但历经一切之后,这份名之为“爱”的感情,却禁锢了他的身体,禁锢了他对大海“始终燃烧的想念”,使他成为“爱的俘虏”。我不禁要问,在更广大的时空和生活中,究竟该如何引导孩子理解“爱”与“梦想”“自由”“亲情”“成长”“友谊”和“责任”之间的关系?认同或获得一种以意识到的自我牺牲为代价的沉重之“爱”,对孩子(包括成人)来说,是一种具有拓展力的“成长”吗?诚然,“成长”是生命获得重量的过程,但这究竟应是什么样的重量?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多年来,儿童文学努力克服着“成长”书写中虚幻的理想主义,《星鱼》进一步提出,如何在虚幻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生活主义”之间,寻找通往“成长”的更好路径。
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
如果说原创儿童文学对传统文化资源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创作关注,那么2018年,我们不但继续读到了一大批涉及传统文化题材或思考的儿童文学作品,而且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它正在成为一股鲜明的创作潮流。这其中既有文化政策层面的大原因,也因为在这个技术激进的新时代,如何承续来自传统的悠远文化脉络,如何使日益讲求效益和功利的现代生活在与千百年来积累的传统的对接中,寻找一种匮乏的栖居感,已经成为文化自身的迫切诉求。2018年出版的相关作品,有的带着传统文化教育、传播的鲜明意图,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系列图画书(高洪波等文,程思新等图)、明天出版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画书大系》(保冬妮文,刘江萍等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持续出版的“故事中国”图画书系列(李健编绘)等;有的则是在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故事或生活底子上展开叙说,如《南村传奇》(汤素兰)、《大蟹》(萧袤)、《鄂温克的驼鹿》(黑鹤文,九儿图)、《冬夜说书人》(徐鲁文,王祖民、王莺图)、《野娃子》(董宏猷)、《巫师的传人3:古国羽衣》(王勇英)、《挂龙灯的男孩》(冯与蓝)、《刀马人》(王璐琪)等作品。
一种传统文化的鲜明意识介入儿童文学创作,最易导致命题作文式的写作,也最忌受限于命题作文的阶段或状态。应该看到,在一切传统文化题材的儿童文学写作中,除却传统文化自身的内容、内涵,作家还需思考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这种面向传统的书写所体现的现代文学意义与现代艺术价值。在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鲁迅的“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多年来被人们过度引用附会,造成将传统文化本身与文学(文化)价值直接等同的简单倾向。然而,传统文化的标签本身远未能为文学书写提供充分的价值前提。相反,为什么要写传统,这种传统与现代生活的关联何在,如何观看传统、思考传统,如何在面向传统的书写中实现它独特、重要的现代价值,这些问题,是我们怀着各样考虑进入传统文化题材或背景的写作时,必须审慎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这种思考鲜明地体现在近年汤素兰的《南村传奇》等一系列传统童话再创作的实践中。《南村传奇》以现代幻想小说的方式进入故事,又以中国传统童话的样貌展开故事,传统与现代元素之间既构成对撞的矛盾,也提供了新生的契机。例如,关于天梯的传说,沿用的是民间童话中追求“幸福”和“永生”的古老主题,却在改编中被赋予了鲜活的现代内涵。“在这一个生命周期里,一个人不断成长,为自己的生活和梦想付出努力,然后无怨无悔地离开,便是最大的圆满。”在对古老童话主题的打破和重思中,故事把读者带向了当下生活的深刻思索。
有意味的是,文本中,作家的思考和探索也留下了未完成的痕迹。比如,作品充分发挥了民间童话特有的传奇色彩,但在另一些“破而后立”的地方,则不得不采取更多概括而非具体的叙述:“在这一千年里,他们目睹了人间无数悲剧和喜剧”;“他们的外表虽然还像十来岁的孩子,但心已经非常苍老”。在这里,思想的上升似是以故事性的下降为代价的。而我以为,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故事性的下降,有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思想的表达。“如果他们没有这么长的生命,就不用感受这么多人间疾苦了。”关于“永生”的反思落在“回避痛苦”上,是否又有浅化这一思考之嫌?《南村传奇》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有生长力的。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思考的存在,恰是原创儿童文学不断深入艺术腹地的症候。
毫无疑问,我们还在前往更远方的路上,而一切行程,拥有这样的远方感,既是砥砺,也是幸福。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代表品潮时尚网立场。)








